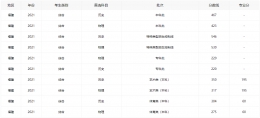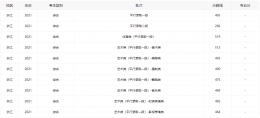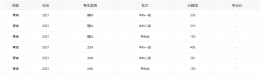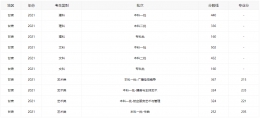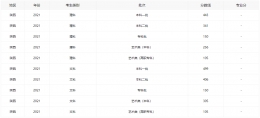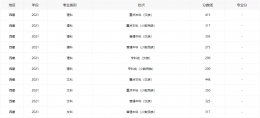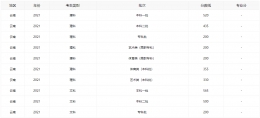您所在的位置: 首页 > 教程首页 > 新闻资讯 > 我们在玩手机,还是手机在玩我们
黄家良分析,手机幻听症的易感人群通常都会频繁使用手机,“往往在铃声一响时就得立即投入工作,这些人长期处于‘待机’状态,强烈的心理暗示会诱发‘幻听’。”黄家良表示,不管是手机幻听症还是社交恐惧症,其成因都是长时间使用手机、过分关注手机而造成的。
专家建议:目前困扰都市人生活的“手机心理病”现象,其实只是人身体出现压力时的一种表现,是身体潜意识给出的提醒,只要摆正心态,增强自信,真诚主动与人沟通,这样压力就会被克服。
由于长时间使用单一的手机铃声,会强化大脑感应,容易幻听,因而经常更换手机铃声有助克服“手机幻听症”,并采用一些相对舒缓的乐曲,以放松身心。

多重任务疯狂症
“我觉得我快要坚持不住了。”杨华宁说。北京秋日的阳光透过国贸宽大的玻璃窗,洒在这位前IT公司高管身上,但却掩不住他苍白的脸色。
杨身上的问题显而易见。即便已经从公司辞职,他手里仍然时时刻刻都在摆弄一部精致的智能手机,在上面刷刷点点,偶尔抬一下头,目光也看着别处。不得不说,坐在对面观察他如何使用手机是一件非常赏心悦目的事,他的手在程序间的切换熟极而流,像是一位魔术师在表演最拿手的段落。而偶尔需要打字时,飞快跳动的手指又像是钢琴师。
如果仔细观察,你会发现他更像是一台精准运行的机器——机器不断将最新的讯息推送到手机,他会每隔30秒打开锁屏查看一次,再过30秒,则会查看一次邮件,而此后则要查看微信和微博等等,又两分钟过去,他又会重复上面的动作,周而复始。
“没办法,已经成了习惯。”过去5年中,杨华宁每天夜里都会被手机吵醒,白天去任何地方,都要携带3个充电宝为手机充电,随时拍拍口袋看看手机在不在,已经成为他的标志动作。在任何一次或长或短的出游计划中,他扮演的角色都是同一个——一个永远低头看手机的旅行者。再到后来,即使再重要的场合,他也没有办法放下手机,直视着别人完成一次对话。
杨并非一个智能手机悲剧的个案。中国工信部最新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,中国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已经超过8亿人,其中超过3亿人,是和杨华宁一样的3G智能手机用户,后者还在以每个月将近1000万人的速度迅速增长。
即便发展速度慢于中国,国外的情况也并未好到哪里去。《英国每日电讯》援引babies网站的一项调查说,他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英国的父母们,居然会让这些不到1岁婴儿每天玩4个小时iPad——他们每天醒着的时间只有大约10小时!
智能手机的普及显然给所有人带来了困扰。仅仅在这个月,就有湖北一名少女走路看手机而掉入深坑坠亡,而南京一名男子则因为专注于手机挡住了火车。重庆的一位学生家长,则为儿子所在的学校捐赠了40万元的非智能手机,希望创造一个没有智能手机骚扰孩子的“正常成长环境”。
杨去看过心理医生。医生的看法与拉里·罗森在他的《i成瘾》一书中定义的情况基本没有太大出入,即这是一种典型的“多重任务疯狂症”,具体而言的症状是,“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网络使用者,在网上进行阅读或者进行超文本文档读取时,也很容易分心。”最典型的案例是,“在收到信息的两分钟内,就强迫自己回复”。
这位加州大学心理学教授还在书中定义了手机成瘾的其他一些症状,例如“手机震动幻想症”,“讯息查看强迫症”以及“缺乏睡眠喜怒无常症等”,认为手机成瘾是一种“低自尊”导致的精神疾病,与财富滥用和病理性赌博类似,成瘾的人们通常“利用强迫行为来摆脱强迫观念”。他甚至援引了一份研究数据,指出成瘾者和非成瘾者的大脑系统在灰质和白质上都存在明显区别。
但杨华宁的问题在于,除非所有人都放弃智能手机,否则作为一个45岁的中年中国男人,无论是否在工作,他都无法承受没有智能手机的生活。
另一种人格
这个问题似乎无解。美国的一篇论文曾经依据“五型人格”理论研究认为,外向型的人更倾向于拥有智能手机,并且对短信功能需求更高;而亲和性的人更倾向于打电话而不是发短信。换句话说,是否更容易“上瘾”,与个人天生的体质有关。
至少就吴若曦而言,这个理论并不足够成立。工作日的温哥华国际机场简直一团糟。广播在头顶一遍又一遍地last call,眼前是成群不知所措的旅客,耳机里是流水一样发来的指令,充斥着各种调度、术语、程序和令人抓狂的混乱。
但作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的毕业生,刚刚工作6个月的机场地勤,吴若曦已经对此驾轻就熟。半年来她已经保障了104架航班的起飞。她在值机柜台闲庭信步,甚至还用空余的时间跟朋友分享了航空公司的新机型,解答了一个陌生朋友的感情问题,就最近国内的一桩热门媒体事件发表了感想。
值得一提的是,完成这一切不需要任何其他工具,除了一部智能机。
这对吴这样重度的手机用户来说,不算什么。毫不夸张地说,吴的生活就在手机上。她已经习惯“一心二用”的生活——每天起床要先看10分钟手机资讯,吹头发的时候也在看,路上在看,工作的时候在看,下班之后还在看,即便有朋友聚会,大家也都在看手机。今年6月的苹果发布会,时间上正好跟某个航班撞车,吴若曦甚至还作为某国内网站的解说嘉宾,在百忙中用手机完成了全程直播。
这件事的结果好坏参半。一方面,这个在手机上叫做“Onlyswan”的女孩,拥有13000名Twitter粉丝和30000名新浪微博粉丝,拥有一个手机上认识的老公,甚至婚礼上的嘉宾,也是手机上邀请来的。但另一方面,因为有十几部不同品牌的手机轮流使用,临睡前找不到其中任何一个的充电器,带来的焦虑感都会让她失眠。
更多的困扰可能来自于现实与虚拟的割裂。当亲戚、朋友、同学甚至顶头上司,发现吴在手机网络上那些尺度很大的自拍照,尺度很大的两性话题讨论,以及尺度更大的涉及政治的言论时,无不惊讶于那个平时只顾低头玩手机的怪女孩,居然在手机上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吴只能对此摊摊手,“只能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,也许这是个最好的沟通方式吧。”
但这些对吴来说都并不是问题。她参加过许多线下聚会,认出她的网友并没有更多进一步的冒犯举动。他们对她的价值观表示尊重,甚至激赏。尽管曾经被网警请去“喝茶”,但她并没有因此感到困扰,最近甚至还有一位某地级市的网警在微博上对她说,等她回国要过来见面,像朋友一样,就很多问题当面探讨。
吴若曦觉得她从智能手机中获益良多。在2008年开始使用智能手机之前,她就已经混迹于各大论坛,是个小有名气的宅女。现在的她依然怕打电话,但会更多走出去,更多与人打交道,她甚至已经辞职,决定在互联网圈子里做点事情,甚至拣起“国际政治”的老本行。这有什么不好呢?
很明显,我们多数人都并非生活在荒岛上,也并非卢德派教徒,与手机打交道不可避免。最近出版的新书《与手机同床》讲述了以苦干著称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如何与7/24小时在线工作斗争的故事,办法是强制提高效率,早点下班。
《经济学人》并不认为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手段,“情况只会越来越糟”,文章说,“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智能手机厂商和应用厂商们,主动把手机‘非智能化’。”